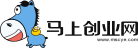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李诚脸上,他盯着后台那个跳动的“已付款”字样,指尖无意识地在键盘边缘摩挲。
这是他开网店卖手作以来的第一单,金额不大,地址就在邻市。
但这个消息却像往平静的湖面投了颗石子,漾开的涟漪从屏幕蔓延到心口,连带着呼吸都变得轻了几分。
此刻,李诚仿佛又看到了陈爷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指关节粗大,却能让柔韧的竹篾乖乖听话,编出细密又结实的纹路。
还有张奶奶,上次去收剪纸时,她正坐在窗边的小板凳上,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她颤抖却精准的指尖上。
红纸在她手里翻折、裁剪,剪刀开合间,一只栩栩如生的喜鹊就跃然纸上。
她当时笑着说:“这剪纸啊,得有耐心,急不得。” 李诚看着她案头堆着的一沓红纸,边缘有些毛边,那是无数次练习留下的痕迹。
“原来,真的会有人懂。” 李诚心里想道。
这单生意或许很小,但对他来说,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做的事有了意义——让那些被时光藏起来的手艺,重新被人看见。
第二天一早,天刚蒙蒙亮,李诚就揣着那个剪纸往村东头的张奶奶家走。
他远远就看见张奶奶坐在院门口的竹椅上,背对着他,正眯着眼晒太阳,手里还捏着根线头。
“奶奶!” 李诚喊了一声。
张奶奶回头,看见他,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:“哎哟,小诚来啦!快进来快进来,今早特意煮了糖水,给你盛一碗。”
李诚被她拉进屋里,一股淡淡的糖水香扑面而来。
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个粗瓷碗,里面沉着几颗饱满的红枣,糖水还冒着热气。
他没顾上喝,把手上那张剪纸递给她:“奶奶,这单您帮我包装一下吧,下午快递员来取。”
张奶奶接过剪纸,枯瘦的手指轻轻捏着边缘,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。
她把剪纸平铺在桌上,转身找出一个干净的棉纸,又从床底拖出个旧木箱,翻了半天,找出个印着蓝格子的小纸盒。
“得把这剪纸裹三层棉纸,再放进这个盒子里,外面再缠上泡沫,可不能磕着碰着。”
自从这第一单之后,李诚的网店就像被春风吹过的种子,慢慢发了芽。
起初只是零星几单,多是邻市的客户,但渐渐地,订单开始往外地走——北京的姑娘买走了陈爷爷编的菜筐,说要带回去给妈妈当收纳篮。
上海的情侣买了张奶奶剪的“囍”字,说是要贴在婚房的窗户上。
广州的宝妈买了木梳,评论说“给孩子梳头不打结,比超市买的好用多了”。
日子一天天过,李诚每天的生活被打包、发货、回复消息填满,却不觉得累。
他会定期去陈爷爷家,帮着整理竹篾,去张奶奶家,看她剪新的花样。
三个月后,他的网店有了回头客。
那个买了张奶奶“喜鹊登梅”剪纸的北京姑娘,又发来消息:“老板,还能再买一张吗?我闺蜜结婚,我想送她这个,觉得特别有意义。”
半年后的一个清晨,李诚是被手机“叮咚叮咚”的提示音吵醒的。
他迷迷糊糊地摸过手机,屏幕亮起来的瞬间,他差点没反应过来——后台消息99+,屏幕顶端的数字从“1”一路跳到“127”。
“127单?” 李诚猛地坐起来,心脏在胸腔里“咚咚”直跳,仿佛要蹦出来。
他顾不上穿拖鞋,光着脚冲到电脑前,后台页面密密麻麻的订单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地址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,一直到新疆、西藏、黑龙江,连偏远的小镇都有订单。
还有人在备注里催单:“老板,能不能快点发?我女朋友等着用呢!”
三个月前,他还在为一天能接到两单而偷偷开心,现在127单,是那时的六十多倍。
他想起第一次收到订单时,自己对着屏幕傻笑了一晚上。
现在,看着这些订单,他忽然有些不知所措,这么多订单,他能忙得过来吗?那些手艺人,他们能跟上这个节奏吗?
接下来的几天,订单量没有丝毫减少,甚至每天都在涨。
李诚开始犹豫,他是该趁机扩大规模,招聘几个员工,租个大仓库,开个实体店,还是继续保持小而美的模式?
那天晚上,他去陈爷爷家送新收的竹篾。
陈爷爷正在编一个更大的竹筐,竹篾在他手里灵活地穿梭,发出清脆的“咔嗒”声。
李诚坐在旁边,看着他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滑下来,轻声问:“爷爷,您觉得……现在这样好吗?订单越来越多,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陈爷爷停下手里的活,抬起头看他,浑浊的眼睛里盛着光:“小诚啊,编筐和做人一样,不能贪多。竹篾要一根一根编,急了就容易断。老手艺这东西,就像这竹条,得慢慢磨,才会有韧性。”
李诚沉默了,他想起张奶奶,每次剪“囍”字,都要对着样子反复比对,一个线条不对,就拆了重剪,一张剪纸往往要花上大半天。
如果订单多了,张奶奶是不是要熬夜赶工?那些带着温度的手作,会不会因为赶时间而失去了原有的细腻?
回到家,李诚坐在电脑前,看着屏幕上还在不断跳出来的订单,心里忽然有了答案。
“对,就保持这样。” 李诚在网站上发了一条消息:“感谢大家喜欢我们的手作,为了保证品质,我们每天的订单量不会超过50单,还请大家耐心等待。”
发完消息,他靠在椅背上,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,落在桌上那个陈爷爷编的小竹筐上,筐里的绿萝正舒展着叶子,一片生机勃勃。
他知道,这条路或许走得慢一点,但只要初心还在,那些带着温度的手作,就会像村口的老槐树一样,在时光里慢慢扎根,细水长流。
 上海
上海